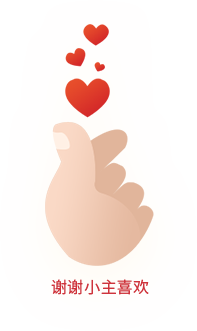对话凌宗伟:阅读,给教育带来改良
《中访网》特约记者 亚东
人物简介:凌宗伟,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校长、中国教育报刊社签约评论员、《中国教育报》“2012年度十大读书推动人物”之一。江苏省教育学会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教师博览》兼职编辑。做过四年高中教务处副主任、13年高中教学副校长、6年校长,2013年8月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校长位置卸任,现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语文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学校管理、语文教育、家庭教育。民国教育家刘百川研究者,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受邀在全国各地讲学,语文教学主张“遇物则诲,相机而教”,形成了“大气磅礴,细处摄神”的教学风格。近年来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中国教育报》等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四百多篇。先后在《教育家》、《今日教育》、《教育视界》、《班主任之友》、《教育时报》、《中国教育报》设有专栏。有专著《好玩的教育:学校文化重建五讲》《阅读,打开教育的另一扇门》《有趣的语文:一个语文教师的“另类”行走》《语文教师的使命》、《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编著《校长之道和人格修炼》《健康教育》《成长的烦恼》等。

《中访网》特约记者亚东与凌宗伟在一起
亚东,平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印度尼西亚三语教学促进会特约顾问,中国教育电视台果实网新闻社区评论员,中国访谈网特约记者,《平凉教育》副主编、责任编辑,1999年签约北京墨溢香文化公司,2002年签约北京国道数据电子图书库编辑组,2003年签约北京时代教育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就职教育,2012年曾受中国海外文化交流协会推荐、国务院委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交流一年,出版独著、合著多部,著作曾获首届崆峒文化奖优秀图书奖。
亚 东:阅读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所教的学科不一样,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一样,每个人的阅读取向自然也不一样。作为教师的阅读,如何处理阅读个性和从业需求的关系?应关注到哪些阅读共性?有哪些注意事项?
凌老师:就阅读的共性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回到经典源头去,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等均应该涉猎一些。不管是何专业出身,也无论兴趣点多寡,共通普适且具有一定上位意义的经典之作,都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关注“上下游”:“上游”即教育哲学,如《理想国》,她对建立个人的教育观、学科观将产生深远影响;“下游”即操作性书籍,有实践指导意义。
另外,阅读的共性还指:与教育领域有一定交集、甚至无交集但有借鉴意义的书,也应该读。一个合格的学科老师,只读本学科的书注定不够的;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只读教育领域内的书也是浅薄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媒学、脑科学……这些都是丰富学养、提升品质的领域。教师们应多留意。
至于阅读的注意事项,我以为,首先,自己得有鉴别力。比如,有些书是不能读的,读得越多,可能受害越深。比如国人那些大谈教学模式神话、大谈高效课堂奇迹的,翻翻或许可以,但如果信以为真,则可能会使我们走向反智,甚至反常识的境地,对这些货色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还有那些人人称赞、貌似处处正确的所谓畅销书、鸡汤文,也是值得警惕的。其次,是要兼顾“学以致用”和“用以致学”的统一。前者指不要死读书,需尽量联系和指导自己生活、工作的实践;后者指在实践中产生问题,进而在阅读中寻找启示。这两者共存,方可处理阅读个性与业务需求的统一性问题。
亚 东:教育者应秉持怎样的阅读伦理?
凌老师:关于阅读伦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不要以古非今,东西对立。阅读带来的不是迷信与盲从,她提供的是一种可能的理论,即按照波普尔说的,知识是“可证伪”的。一旦我们看什么信什么,尤其是迷信古代、迷信西方、迷信专家,本身就跑到了阅读的反面去了。
第二是不要责全求备,不妨读一点是一点。一本书能有一个观点、一句话使人的精神生命受益,已经不错了。要小心“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仅仅和一本好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阅读者本身的经验、修为到了相应的水平有关。实际上,真正评价一本书是不容易的,因为情境、立场、历史条件、技术条件均不同。所以,不要指望会有让人拜服的奇书。
第三是阅读需用于实践,尤其是教育阅读,一定要和实践相结合,和常理、常情有关。“阅读理解教育,阅读明白管理”,关键在“明白”与“理解”,这当中自己的取舍是关键,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帮助自己想明白了再做,或者将正在做的和已经做的想明白。我不是讲阅读要有功利性,而是说她必须要有知行合一的可能。无论是书的原因,还是读者的个体因素,凡不能行知合一的,恐难成为理性阅读。当然,消遣式的阅读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亚 东:疾行的教育使我们很少有时间审视人生,审视自己的教育行为,也没有时间静下来反省自己的生命,也问不出深刻与广泛的问题,对于这种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如何通过阅读化解?有哪些推荐书目?
凌老师:就现在的状况而言,老师们多忙着“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学生的学业、个人的职称、家庭的羁绊等。更不要谈深刻而广泛的问题。这一状况,除了种种压力外,没有形成有效的阅读习惯也是一大障碍。要解决这一问题,在现行的框架与格局下,有一个“组织”“推动”“宣扬”的问题。
至于推荐书目,其实是要慎重的,就我个人而言觉得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康德论教育》、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爱弥儿》、甚至穆勒的《功利主义》等都可以读读。
亚 东:互联网时代是自媒体时代,朋友圈式的微阅读盛行,大众化口味、励志化包装、快餐式鸡汤文和“钙片文化”充斥在阅读中,看似正能量满满,却带来认知水平降低,对此,您认为应该“啃一点难啃的书”,调动阅读者的“社会资本”与“决策资本”来帮助自己扫除阅读的障碍,能谈谈您的具体建议吗?
凌老师:如前所说,我以为首先是要警惕畅销书。这种类型书,除了可能炒起来的以外,本身就是大众化、忽悠化、鸡汤化的。二是净化朋友圈,寻找优质资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人的朋友圈自然有不同的阅读取向。我一直主张要“啃一点难啃的书”,这就需要有一干“少数派”的朋友。朋友圈除了有“补钙”的短视利益外,也有一些难啃的、启智生益的佳作被推荐、被谈论。三是读书贵质不贵量,有时候读得汗牛充栋倒不如人家迎头一喝,正是这个道理。
“啃书”的意思有两重:一方面是说“选择大于努力”——再努力认真,如果当初选了本有害的书,后果不言自明;一方面是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韧性,读书不能速成,凡是宣称一年读了多少多少本的,一笑即可。关键是,“啃”好一本书的背后,常常需延猎相关学科、领域的多种书籍,读到最后就成了一摞书、一批书了(“从薄到厚”),即所谓的“主题阅读”。而这一摞书、一批书,不需要本本句句字字读透,只需围绕“元问题”的核心即可,读没读通又可以从能不能缩书成句、缩句成词来体现(“从厚到薄”)。凡不能简明扼要的以大白话抓住主旨者,都因为“啃”不到位的原因。所谓“啃”还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在里面。
亚 东:阅读需要联想和想象参与其间,要在文字的前后勾连中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寻找表达的脉络,判断文字的价值,获得新的认知。在纸质阅读变得奢侈的今天,如何处理阅读中“熟与透”、“厚与薄”、“小与大”、“知与行”的关系?
凌老师:这个问题,在前述中已做过回答,再补充一下:我们对经典读本,有一个定义:每次重读,都如同一本新书。“熟与透”“厚与薄”“小与大”等关系,说到底,就是“体”“用”的统一与变异,由“不兼容”到“阵痛”,再到“融一”的内化过程。
渡过这个过程的要义,即是前面的阅读伦理所说的,一定要坚持从“学以致用”到“用以致学”的反复螺旋。为什么说每一次读来如“新书”,新在哪里,无外乎是在经验匹配中出现了问题,而经验匹配又一定出自于实践。
亚 东:为了内化读书效果,您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建议?
凌老师:我首先要说的,是形成一个“自组织”:自发的、有共同诉求、有共同兴趣的但不是利益诉求的“小团体”。这对“内化效果”有着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读书不一定要一个人闷着头做苦行僧,他人无心之言,或许正是你苦苦求索而不得之处。其次是不动笔墨不读书,这虽然是老话,但“知道”和“做到”还是两码事,我强调的是做到。第三是要写写读书笔记、书评等。在时间上,可以整块整块的处理,也可以随性而为,但要发挥最大效能,笔记最好是一系列的,结构化的,规模化的。你可以对应原书章节,也可以对应自己的感悟,甚至是自己分的主题,关键在各人的需要。
在形式上,也不限于上述几种,可以每每有收获,做成一个PPT,慢慢地形成整套的PPT;这种方式,以简要的文字、图表来表达自己感悟,说不定效果更佳,因为更直观嘛,而且重点、难点一看便知。当然,也可以使用一些便捷、有效的软件,比如“图书笔记” 。
亚 东:教师的浅表阅读,浅表教学,必然导致学生的浅表学习,教育者喜欢上阅读的时候,教育才能“慢”下来并形成一个漫长的浸润过程,教育的改良才能成为可能。您认为这种改良可能包含哪些内容?教育者“开始用内心的耳朵去倾听”的时候,如何实施改良?
凌老师:这里,许多时候,教育不是慢下来就好,快起来就不好。教育真正应该遵循的是其本身的节律,或许教育本就无所谓快慢之分,因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今天,之所以让教育变得“慢”一点的声音更易被大家接受,实在是功利和浮躁的社会现状使然,这一点我理解。但其实某种程度上说,慢了和快了一样,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还是源于对教育的本质与价值,甚至是常识的认识的偏差所至。
说到改良,我以为至少有:评价的进步(由结果到过程,由单一到多元,由异态到常态)、课标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变革、测量的科学化和人文化、管理的民主化。一言以敝,未来的教育改良应该有“非效率化”(不少不唯“效率”是从)的重要特征。
怎么做?除了“自上而下”的改良,“自下而上”的自主意识觉醒可能更具现实意义。由阅读为中心,衍生出的论坛、写作、课题、演讲、辩论,乃至于一定范围内的游学、互访、实验,甚至新技术条件下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端等)等,均可能成为推动这一改良的助力。但是这些形式,同样可能催生另一种有违教育价值的一些行为。这是我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各位同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需要读点关于伦理方面的书籍的原因。
老实说,教育领域中,包括阅读在内,生态都不是特别好。但既然认准了自己的选择,则“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时代给我们,还是留有不少机会的。
亚 东:确如您所言,当前的教育领域或阅读氛围,口诛笔伐的多,尝试改变的少,夸夸其谈的多,潜心实干的少,很多人期待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带来一蹴而就的改变,似乎一次课改就能一劳永逸,似乎一本好书就能函盖乾坤,却忽视了自己本来就是教育业态的一部分,自己的些微改变就能带来教育的改良,千千万万普通教育工作者做出改良,就是整个教育生态的改善。谢谢您。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ID:ctoutiao),给您更多好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