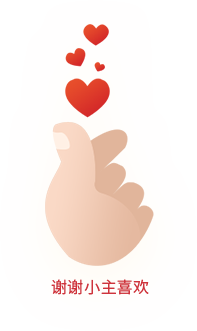无国界医生战地实录:交火双方伤员同时救,进医院先缴械
© Mikhail Galustov,无国界医生急救室医生在阿富汗昆都士创伤中心为一名伤者实施抢救。
文|八点健闻,作者|毛晓琼
“无国界医生”创立于1971年的法国巴黎,旨在为受冲突、疫病、天灾、人祸影响的地区提供无偿的医疗援助,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之一。“无国界医生”不隶属于任何政权或政治、经济、宗教团体,他们秉承“中立、独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对危困人群提供一视同仁的救治,1999年获得世界诺贝尔和平奖。
过去一年,“无国界医生”的项目遍及70多个国家,其中超过半数项目是在武装冲突、内部局势不稳定或战后地区开展。在中国内地,总计有40多名救援人员通过“无国界医生”的考核,进入后备人才库,处于随时待命状态。
八点健闻近日访问了一位来自广州的无国界医生赵一凡,他曾在2013年4月至6月间,参与了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昆都士创伤医院的前线救援任务。该医院在2015年被美军炸毁,造成至少14名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死亡。
本文系八点健闻根据被访者口述整理写作而成,为更真实展现被访者的经历和感受,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
以下为叙述要点:
看了“无国界医生”纪录片而感动,自己也成了一名无国界医生。
接到任务时,心情复杂。有期待,也有对危险的担心。
到达阿富汗当天就抢救了一位被子弹打穿肾脏的妇女。
直面生命脆弱。一位8岁受伤女孩,4次手术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两年后,所在医院被美军轰炸,14名无国界医生死亡。
抢救别人的人,最后连自己都不能幸免。
总有一些东西应该凌驾于政治之上,比如治病救人。
接到任务那天,我心情复杂
我第一次知道“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是在2012年。那年7月,我和太太偶然看到了旅游卫视一档《行者》的节目,播了6期与“无国界医生”有关的纪录片。纪录片主角之一是一位名叫邹有铭的香港急诊科医生,他参加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来到南苏丹一个叫皮博尔的地方,住在帐篷里,给附近20万村民免费治病。当时他才20多岁,是当地唯一的医生。
我俩看得眼泪汪汪的,因为我们都是医生,很容易被那种纯粹的理想感动。那时候,我在广州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工作了10多年,刚刚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你知道,大型三甲医院高强度的工作,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那天,我和我太太四目相对,没等我开口,她就说,如果你想去的话,就去吧。
那年的8月底,我就在“无国界医生”网站上填了报考信息,很快就收到了通知,并参加了几轮考试。最后一轮的面试地点在香港,是我太太陪我去的,考题还挺难的,考完已经是一头大汗。没想到过了大半个月,我接到了录取通知。
2013年1月,我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到阿富汗昆都士省的创伤医院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前线救援。
现在回想起来,接到任务的那一天,我心情挺复杂的。首先,当然是期待,毕竟是自己很想做的事,也为之付出了努力,等来了梦想成真的时刻。其次,有点担心。阿富汗是一个充满武装冲突的伊斯兰国家,曾经有5名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执行人道救援时被杀害,导致无国界医生退出这个国家长达5年之久。再加上我的女儿当时刚出生不久,于情于理我都不应该离开。
于是,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两边的老人简直炸了,一致反对。后来还是我太太坚决地支持了我的决定。
抵达当天晚上就做了第一台手术
2013年4月6日下午4点多,经过3天的辗转和颠簸,我终于抵达了阿富汗昆都士省。昆都士位于阿富汗北部山区,是阿富汗第5大城市。尽管医院就在市中心,但当地的马路、建筑和风土人情,更像我小时候待过的中国农村。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和端着枪的士兵。
红圈处便是阿富汗昆都士省
我对昆都士创伤医院的第一印象还不错,毕竟不是扎在野地里的帐篷医院。医院里总共有两间手术室,设备很简陋,手术使用的麻醉监护仪和麻醉剂,都是过时很久的产品,可能连我的老师都没见过。我一度以为,设备简陋是因为缺钱。后来才知道,选用这些基础款的设备,是为了保证损坏时更容易修理。设备的可及性,是前线救援的第一准则。
我在阿富汗的第一台手术来得很突然。抵达医院的当天傍晚,我刚刚领了值班手机回到宿舍。洗澡洗了一半就听到手机在响,医疗统筹在电话里很着急地告诉我,一名本地妇女腰部受了枪伤,子弹打穿了她的肾脏,急需进行剖腹探查和肾切除手术。
△图片来源:赵一凡/MSF在阿富汗,赵一凡和外科团队们在两个月时间里完成了500多台手术。
我赶到手术室的时候,其他医护人员都已经就位了。我扫了一眼,外科医生是丹麦人,另一个麻醉医生是希腊人,麻醉护士是当地阿富汗人。大家的英语都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所幸我的专业英语词汇量还可以,配合具体的场景,第一台手术还算顺利完成。 这位妇女醒过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手术做了吗?”我当时心里很高兴,因为她在手术中没有任何感觉,说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麻醉。
同时收治敌对双方势力的伤者
在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后,节奏就变得非常快,当地需要做创伤手术的病人实在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那儿的孩子特别容易受伤。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阿富汗的家庭普遍会生很多小孩,家长管不过来,就让孩子自己在外面玩,到了饭点回家吃饭就行。我曾经见过一个小女孩,跟着哥哥去耕地,一个不当心,三个脚趾头就被剁掉了。
MSF149194© Andrew Quilty/Oculi这名4岁的小女孩从屋顶上摔下来,摔断了腿,被父亲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曾经救治过一个2岁女孩。送来的时候,上下颌骨骨折,右嘴角撕裂达颧骨,伤口血流不止,必须咬着一堆纱布减少失血。她一直流泪,连张开嘴哭的力气都没有。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大家都很犯愁,这么小的孩子,面部伤势又那么重,麻醉和手术都很难进行。丹麦的外科医生说,实在不行,我们就做气管切开吧,上全身麻醉。
这个手术其实很难,2岁的孩子,那么小的脖子,那么细的气管,对任何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成功率都不会太高。 后来,我提出可以尝试“经鼻气管插管”的办法,这是我在国内做头颈外科手术时积累下的经验。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办法的风险也很大,它要求麻醉医生的手要快且准,止血纱布一拿开,就要迅速把管子经过鼻子插到气管里去。但凡慢一点点,血流进气管,病人就会窒息死亡。
感谢上帝!那天插管很成功。
90分钟后,骨折部位固定,口角撕裂被美容缝合,气管插管移除,小女孩在无痛苦情况下苏醒,手术成功了!那一晚,在手术室里,大家击掌相庆,有人唱歌宣泄情绪,也有人和小女孩的父母抱成一团,哭成了泪人。 在无国界医生的工作守则里,中立和不偏不倚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同时收治敌对双方势力的伤者。 我们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先是收治了一名当地警察,这位警察在与反对派的对抗中,被炸掉了两条腿,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失血性休克中抢救回来。
结果没过两天,我们又收治了另外一位病人,有人说他是当地反对派武装力量的一位士兵,中了枪伤,来做腹部清创手术。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两个病人同时在病房中接受治疗,但相安无事,直到反对派的那个士兵先一步出院。这就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立场,不偏不倚,认同每个人都有得到医疗救治的权利。
© Michael Goldfarb/MSF无国界医生的医院、宿舍门口,以及来往车辆上都有无国界医生的标志以及武器不得入内的标志,以确保组织的中立立场。
当然,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比如在医院门口、宿舍、救护车辆上贴上无国界医生的标志,以及“武器不得入内”的告示。所以,你有时会看到,有的士兵被同伴搀扶进医院之前,要把身上背的火箭炮或枪支卸掉,军装脱下来,专门留一个人在外面看管或带走。这一点,是“无国界医生”项目得以在当地开展的底线,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保护。
图片来源:赵一凡/MSF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上不会寻求武装保护,医院门口会有武器不得入内的标志,说明组织的中立立场,救援人员也会穿有组织标志的衣服。
8岁受伤女孩因发生肠瘘而离世
无国界医生的工作,很容易给人带来满足感,也很容易带来失落感。我们救活过很多伤者,也免不了看到其中的一些人在我们眼前离世。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巴斯敏娜的8岁女孩,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天,她跟着父母去参加一场婚宴。结果婚宴上发生打斗,巴斯敏娜被流弹打中了腹部。
她被送来医院的时候,肚皮被割开了,肠子流在外面,她的父母用一条红色的毛毯把她裹住,辗转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送过来。我们用了最大的努力去抢救她,给她输血,并把库存的最后一条中心静脉导管用到了她身上。 在8天时间里,她坚强地接受了4次手术。在做完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她还高高兴兴地边吃香蕉边和我们聊天。但到了第二天,她的肚子开始发胀。我们打开她的腹腔,确认了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巴斯敏娜发生了肠瘘。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伤口愈合需要营养,而肠道是吸收营养的器官,偏偏伤口又长在肠道上。于是,病情陷入了死循环。在医疗条件稍好一点的地方,可以通过静脉注射营养液来促进伤口愈合,但在昆都士,小女孩只能通过吃东西来获得营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巴斯敏娜最后几乎是饿死的。
COME AND GO,在昆都士创伤医院,我们每天都要目睹大量的生命,在前一刻到来,后一秒离去。这也是无国界医生的经历,赐予我最宝贵的财富——让我真正明白生命脆弱,活在当下。
MSF149178© Andrew Quilty/Oculi一名小病人和父亲一起在医院里等候接受X光扫描。
抢救别人的人最后连自己都不能幸免
如果满打满算的话,我在阿富汗待了66天。 我们一周工作6天,每周五放假。但因为当地紧张局势的原因,我们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多的就是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聊天,聊各自的工作,聊自已国家关于医疗的那点事儿。偶尔有外向一点的同事,会用手机放放歌,还特别豪迈地给我们来上一段歌舞表演。我们还看过两次投影电影,直接把画面投影到隔壁房子的大白墙上。对了,我们还踢过一次足球,是在看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
图片来源:赵一凡/MSF赵一凡在昆都士创伤医院的同事们来自不同国家,有些至今仍保持联系。
在昆都士的两个月里,我交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骨科医生,跟我年龄相仿,特别热情。他告诉我自己去过广东,还给我看手机里在肇庆七星岩拍的照片,真的是亲切感爆棚。还有一个是护士长,一个南非的老太太,现在应该已经快70岁了。她是无国界医生里的前辈,出过很多次任务,她和我分享了很多一线救援的心得体会,我很钦佩她。
图片来源:赵一凡/MSF赵一凡和外科团队的同事合影。
2013年6月,我结束了阿富汗的救援任务,回到了广州,和亲人团聚。记得刚回到家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昆都士创伤医院里又来了一个急诊病人,我正打算给他做术前检查。突然,我太太一把把我拍醒了,问我为什么摸她的肚子。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已经回家了。
两年后的2015年10月3日,美军向阿富汗昆都士创伤医院投下了211枚炸弹,造成至少42人死亡,包括14名无国界医生、24名病人和4名病人亲属,其中就有和我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兄弟。
© Andrew Quilty2015年10月3日,无国界医生的昆都士创伤医院被炸毁,组织停止在当地的工作,直至得到各方保证会尊重医疗设施后,于2017年在当地开设诊所。
后来我才知道,空袭发生前4天,“无国界医生”组织还向美国军方多次提供了医院的GPS坐标,重申其所在位置。得到各国认可的《国际人道法》早已规定,即使战争也有底线,冲突各方都不得攻击医疗设施、医疗人员、救护车辆,但美军还是向医院投下了炸弹。
2017年,在得到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尊重医疗设施中立性的承诺后,无国界医生才回到阿富汗昆都士,开设了一个门诊,为伤势或病情较轻的病人提供医疗护理,并在昆都士外运作另一间小型诊所。
我曾经多次接到过任务邀请,但因为要照顾孩子都放弃了,每一次SAY NO的时候,心里都特别遗憾。我和太太商量过,等到以后小孩长大了,如果还有任务找到我,我一定要大声SAY YES!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

钛媒体 App
13965篇文章TA的动态
2022-09-14 钛媒体 App发布了 《星巴克加码中国市场,未来三年要新增开3000家门店|钛快讯》的文章
2022-08-11 钛媒体 App发布了 《白云山麾下公司虚抬药价“把戏”,被拆穿了》的文章
2022-07-06 钛媒体 App发布了 《为了帮00后卷王找到工作,简历修改师们拼了》的文章
2022-07-06 钛媒体 App发布了 《威尼斯向游客收“进城费”,国内城市如何借鉴?》的文章
2022-03-25 钛媒体 App发布了 《蔚来2021年财报发布:年营收361亿元,整车毛利率达到20.1%》的文章